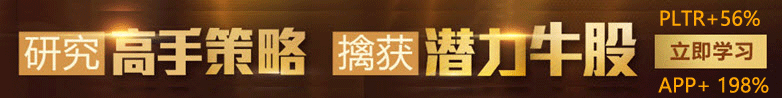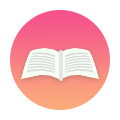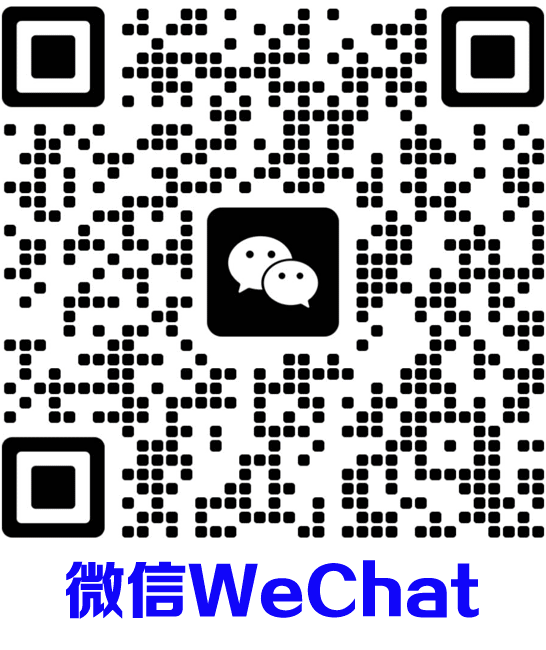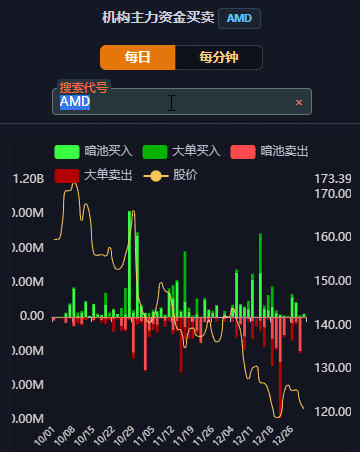在这场关税战之下,美国可能要为它付出高达20万亿美元的经济代价——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经济模型算出来的现实成本。问题是,这笔账到底谁来买?是被征税的外国企业?是美国本土的公司?还是每一个在超市刷卡的普通人?
而就在科技股全线暴跌的同时,有没有一些关税避风港公司或关税利好股呢?今天视频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几只。
大家好,这里是美股投资网,2008年成立于美国硅谷,由前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分析师Ken创立,专注AI,挖掘美股投资机会,旗下 AI量化美股分析工具- 美股大数据 StockWe.com 每天追踪机构主力资金买卖情况,多空情绪。
一场20万亿的代价
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警告称,特朗普提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可能会让美国付出高达20万亿美元的经济代价。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美国一年GDP的七成,或者说,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被蒸发”超15万美元的财富。
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许多经济研究机构,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盛、野村证券等,早就对类似的关税政策进行了深入评估。根据这些机构的测算,如果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关税,未来3到5年内,美国的GDP可能会下降3.5%到4%。这些估算已经算是比较保守的了。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提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带来比以往更大的经济损失?原因在于这次的加税力度更大,涉及的国家范围更广,持续时间也更长。这场关税冲击可能带来的是“结构性下行”效应——即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压低。
萨默斯提出的“20万亿美元”损失,并非随便得出的估算,而是基于一个叫做“长期产出折现模型”(Present Value of Lost Output)的方法。这个模型在经济学界非常常见,原理也很简单:如果一次经济冲击导致GDP增速永久性地下调,比如每年少增长0.5%,那么这种损失就会逐年累积,最终造成巨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如果每年因为关税政策美国损失1万亿美元的产出,这个损失一旦成为常态,未来15到20年,累计的损失将会逐年扩大。按照经济学模型来计算,最终的现值损失可能高达15万到20万亿美元。这就是萨默斯所说的“20万亿美元”损失的背后逻辑。
以史为鉴,在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试图以此保护本土就业和产业。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该政策直接引发一轮全球性关税报复,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资本流动受阻,最终被广泛认为是加剧美国经济大萧条、延长全球经济危机周期的关键诱因之一。
历史上那场贸易战的路径清晰而具有规律性:
最强经济体率先实施高关税,
次强大国进行对等反制,
多边国家被迫站队、形成集团化对抗,
贸易摩擦扩散至货币与资本市场,演变为汇率战与支付体系紊乱,
全球贸易体系被结构性破坏,制度信任土崩瓦解。
而当下,特朗普提出的“对等关税”政策极可能重演这一历史轨迹。加征10%-20%的全球性关税,并对中国征收超过60%的惩罚性关税,导致美国的平均进口税率将升至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仅次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在这种高关税并遭全球反制的情景下,2025年至2028年,美国GDP每年都将偏离基准情景,最大年度降幅达0.88%。更严重的是,初期由关税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可能在经济需求持续疲软的背景下迅速转向通缩压力与增长停滞,对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就业结构造成全面冲击。
从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看,高关税政策短期可能刺激部分行业“回流”或保护性生产,但长期而言,往往以“效率损失+结构错配”为代价,侵蚀潜在增长率,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球越搞越散,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谁在为这场关税战“买单”?
那么这么高的代价,究竟是谁在为这场关税战“买单”?从表面上看,关税是由进口商支付的。但企业不会做亏本的生意。成本一旦上升,企业自然会顺着供应链,把压力一层层往下传导。进口商转嫁给批发商,批发商转嫁给零售商,最后落到消费者头上。
这意味着,我们在超市的商品标签上,在汽车销售的报价单里,甚至在每一张刷卡账单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那笔“悄悄增加的支出”。
尤其在电子、汽车、服装等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行业,关税冲击更是直击要害。一个原本售价合理的零部件,在征税后价格猛涨,制造商不是减产、换料,就是直接涨价。原本800美元可以买到的智能手机,关税之后可能要1000美元,甚至更高。
这不是猜测,而是实证。2017至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欧盟等经济体大规模加征关税。结果如何?尽管美国对外进口商品的总量没有显著下滑,但美国家庭支付的商品价格却普遍上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指出,在那一轮关税政策实施期间,90%以上的成本,最终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买单。
如今的新“对等关税”政策可能会重演这一幕。根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测算,全面实施关税,美国的物价水平将上涨2.1%到2.6%。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相当于每年额外支出3400到4200美元。你可以把这笔钱想象成一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一辆汽车的全年保险和维修费,或者家庭医疗自付额。无论是哪一项,这都是真实的开销,不是账面上的虚数。
更糟糕的是,关税的“隐性负担”还会延伸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RBC Global旗下的BlueBay资产管理公司估算,新一轮关税可能让通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速降至1.5%。尽管目前不至于立刻引发经济衰退,但消费端的疲软已经显现。家庭支出开始缩减,零售和服务行业的销售额走低,经济活力因此逐渐减弱。
关税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数字的变化,更深远的是对消费者信心和生活质量的潜在打击。它不是一项“无成本”的政策工具。相反,关税最直接的买单者是消费者本身,而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每个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经济环境的持续承压。
关税之下的美股表现
猛烈的关税风暴,让美股市场彻底陷入恐慌。本周四美股市值单日蒸发约 3.1 万亿美元,创下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以来的最大跌幅。
科技股几乎全线溃败:苹果暴跌超9%,亚马逊,Meta跌近9%,英伟达跌7.81%,特斯拉跌5.47%。
为什么这波杀跌会集中爆发在科技板块?关键就在于这些企业与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中国的深度绑定。
以苹果为例,它的生产网络与中国高度耦合。富士康等代工厂每年在中国组装数百万部iPhone,而iPhone又占据苹果营收的一半以上。今年2月,苹果刚宣布了一项高达5000亿美元的美国本土投资计划,外界普遍认为是为了缓和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紧张。但现实是,苹果每年向美国市场运送约5000万部iPhone,而绝大多数仍然来自中国。关税一旦大幅上调,苹果的成本、利润率乃至交付节奏都将受到直接冲击。
亚马逊大约四分之一的零售成本与中国供应链直接相关,这意味着新关税政策一出,亚马逊的产品利润空间将被严重压缩。
Meta其收入结构中包含大量来自中国出海品牌的广告投放。一旦中美关系紧张、跨境投放下滑,其营收势必承压。
至于特斯拉,投资者担心的是整条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不仅依赖中国的零部件与电池生产,更在全球多个市场面临潜在的报复性关税风险。一旦各国纷纷效仿美国征税,其全球化布局将遭受实质打击。
避风港受益公司
对我们投资者来说,重点不只是看清谁在这轮暴跌中受伤,更关键的是找到那些能够扛住压力、甚至从中受益的公司。我们要做的,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挖掘那些具备“关税免疫力”的标的。什么样的公司具备这种能力?本土制造占比高、供应链布局以内循环为主、对中国零部件依赖度低,或者恰恰能从制造业回流中拿到红利的企业。更重要的是,这类公司不仅抗压,还可能因这场政策冲击迎来估值逻辑的重构,成为新一轮资金回流的首选。
比如这次市场大跌中,像可口可乐(KO)、宝洁(PG)、好市多(COST)、麦当劳(MCD)和洛克希德·马丁(LMT)都展现出明显的抗压表现。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特点:运营重心在美国本土,供应链稳、对外依赖低,要么具备定价权,要么直接受益于政策支撑。
KO 和 PG 属于典型的日用消费品龙头,产品刚需属性强,价格具粘性,能有效对冲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COST 属于“高效率、低单位成本”的会员制零售商,强调的是长期节省和品质稳定。在通胀或经济承压时期,中产家庭更愿意囤货、理性消费,COST的“量贩+信任”模式反而更具吸引力;而麦当劳虽然不一定最便宜,但作为高频刚需快餐品牌,在经济放缓时依然具备稳定客流;LMT 则更具战略属性,军工订单不受关税影响,反而因地缘局势紧张而具备额外催化。
零售巨头沃尔玛在这轮关税冲击之下,表现也相对稳健。这关键在于它的业务结构。
根据数据显示,食品和杂货(Grocery)业务占据其总收入的59.8%,而这一板块的供应链高度本土化,几乎不受关税影响。食品杂货作为刚需消费,不论经济形势如何,消费者都必须购买,这意味着即便零售价格有所上涨,需求依然稳定。
此外,沃尔玛的供应商主要是美国本土的农业和食品加工企业,食品进口依赖国外的程度极低。因此,关税对这部分业务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部分收入的稳定性也成为支撑沃尔玛整体财务表现的关键。
相比之下,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品类主要是一般商品(General Merchandise),包括家电、服装、家居用品等,这部分业务在沃尔玛总收入中的占比仅25.8%,即便受到影响,其对整体盈利能力的冲击有限。
沃尔玛的议价能力也让它在面对供应商时占尽优势。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的订单量之大足以让供应商“求着它买”。因此,当关税成本上升时,沃尔玛能够迫使供应商承担大部分成本,而不是让自己或消费者完全买单。正因如此,哪怕关税对某些商品有所影响,最终对沃尔玛整体盈利的冲击也非常有限。
除了供应链调整和议价能力,沃尔玛的自有品牌战略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自有品牌的优势很明显:成本低、价格有竞争力、利润空间大。数据显示,2024一年,沃尔玛旗下五个自有品牌在美国市场的家庭渗透率均超过50%,举例来说,“Great Value”品牌已经覆盖了86%的美国家庭,“Equate”也达到了75%。这些自有品牌的价格往往比全国性品牌低20%-30%,此外,47%的美国家庭会选择在沃尔玛购买自有品牌产品,使其在零售市场中占据显著优势。
与此同时,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也是沃尔玛在关税压力下依然稳健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物价上涨导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寻求价格更具竞争力的零售商,沃尔玛正是这类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在经济承压时期,消费者减少高端零售支出,转向折扣店和会员制商超,例如沃尔玛及其旗下的山姆会员店(Sam’s Club),后者的食品和日用品销售增长更为明显。沃尔玛不仅没有因为关税提高而流失顾客,反而因为消费者的“消费降级”趋势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进一步巩固了其行业龙头地位。
此外,沃尔玛的健康与保健(Health and Wellness)业务,占比12.4%,也是其抗衡关税压力的重要一环。该业务涵盖处方药、医疗产品、眼镜、保健品等,具有高度稳定性。即使经济放缓或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仍需购买处方药和基本健康产品。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医保计划及保险公司通常会承担部分药品费用,使得这一业务的需求对价格变动不敏感。因此,沃尔玛在这一领域的收入稳定性进一步降低了整体业务对关税的依赖。
我们本周还买了另外一只特朗普关税利好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很多工厂都在美国,完全不受关税影响,它还在扩大了现有美国工厂的规模,是一家好公司,而且股价现在在底部位置,市销率不到5美元,估值十分吸引人,如果想深入了解这家公司的详细情况,欢迎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