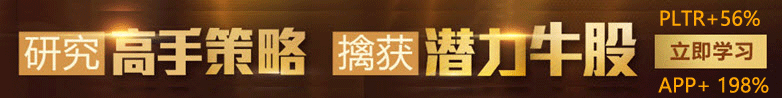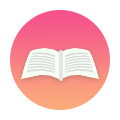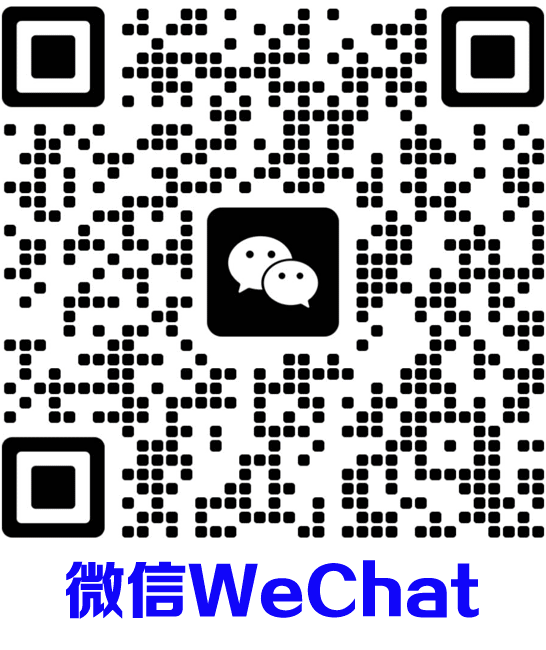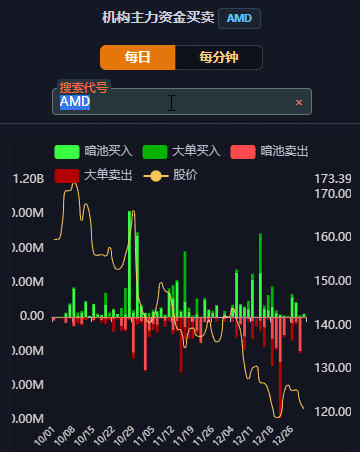美国为何能在一次次经济危机中复苏?为什么美国的资本永远是投资者最青睐的资产,你有想过为什么美股每次暴跌后总能反弹,然后再创新高?本期视频将带你深入了解美国是如何崛起,到建立庞大的金融体系,让你了解到这次关税危机带来的千载难逢机会,在这次抄底美股的过程中更加有信心。
最近美股大数据AI量化团队给各位粉丝派福利了,免费提供美股盘前,盘中和盘后出现异常波动最大的个股,只需官网注册免费账户,就可以立即使用,让你先人一步发现当天交易机会!这里是美股投资网,2008年成立于美国硅谷,由前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分析师Ken创立,专注人工智能和美股量化交易。
美国为何如此强大
美国的崛起,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一战、二战期间,亚洲和欧洲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拼得你死我活,
而美国因隔了一个太平洋,远离主要战场,能专注于向交战国提供原材料、武器、资金和食品,经济越战越旺,积累了巨额原始资本。而英法为首的老牌殖民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力都已经被削弱得不行,无法维持庞大的海外殖民资产,美国顺手捡了一堆大便宜。可以这么说,二战后,老牌殖民帝国退出历史舞台,欧洲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美国凭借着军事和经济实力,稳坐世界老大的头把交椅。自此,美国逐渐开始主导全球秩序。
而关于战后整个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就被提上日程。在1944年7月1日,44国代表齐聚美国布雷顿森林公园,共同签订协议及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者构成新的经济秩序,由此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主导的战后货币秩序,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据统计数据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拥有的黄金占当时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几乎全世界的黄金都通过战争这个机制流到了美国,而美元的霸主地位在这个时候已然确立。
美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全球领先,不到1%的农业人口,却能生产出足以满足本国需求并大量出口的农产品。2023年,美国农业及其相关产业总产值超过1.5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农业强国之列。其农产品出口额达到1749亿美元,为美国带来可观的经常项盈余。
这种高度效率和全球供给能力,使美国不仅早早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更为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的资本与资源支持。
如果说地理与资源,只是美国崛起的起点。真正支撑它走得更远、更稳的,是一整套制度性的优势。美国的政治体系,以“三权分立”为核心,通过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构建出一个高弹性、强修复力的治理架构。自独立建国以来,美国从未发生政权更替式的剧烈动荡,也未出现集权式的专断统治——没有哪一位总统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这种制度上的“去中心化”,正是为什么美国总能在危机中稳住阵脚,快速调整,总能每次走在前面的关键。
更进一步,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长期维持主导地位,还得益于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度掌控。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不再受制于金本位制度的束缚。而通过与中东达成“石油美元”协议,美国使全球能源贸易与美元深度捆绑,从而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今天,全球大宗商品——无论是石油、粮食还是金属——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这意味着:只要全球还需要美元,美国就有能力通过发行货币,获取实际资源。每当危机来临,美联储可以实行量化宽松与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复苏,而其他国家则需承受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的冲击。美元霸权不只是货币问题,它是一种制度性权力——让美国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财政灵活性与经济战略空间。
美国的强大,也深深根植于其持续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战之后,美国通过一系列人才引进计划,吸纳了大批欧洲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例如,在“回形针行动”中,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被引入美国,后来成为NASA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首席设计师,直接推动了美国载人登月计划的实现。同时,包括爱因斯坦、费米在内的大批科学巨匠也在这一时期移居美国,参与原子弹、核能、计算机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为美国奠定了深厚的科技根基。
但真正让这些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的,是美国独有的“大学-企业-资本”三位一体创新体系。从斯坦福到MIT,从哈佛到加州伯克利,美国高校不仅在基础科研方面全球领先,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硅谷等产业中心之间有着紧密连接。斯坦福大学孕育了谷歌、惠普等科技巨头;许多高校设有成果转化办公室和创业孵化器,科研成果能够在数年内迅速商业化,形成产业闭环。
正是这种制度化、系统化的创新机制,使得美国在从互联网到AI、从生物工程到量子计算的每一轮科技革命中都处于浪潮之巅。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研发实力,更体现了其制度对创新的友好度——从风险容忍、人才激励到资本支持,环环相扣,构成了美国科技霸权的底层结构。
历次危机美股如何化险为夷
这些制度与文化的优势,并不仅体现在科技和产业上,更在美国资本市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美股,作为全球资本的风向标,也是一面映照美国经济制度弹性与修复力的镜子。
回顾美股历史,每一次大跌都曾引发巨大恐慌,但也正是这些剧烈震荡,不断倒逼市场机制进化,让美股在反复试炼中建立起更强的韧性与透明度,危机过后不仅迅速修复,往往还能再创新高。
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单日暴跌22.6%,道琼斯市场蒸发超过5000亿美元。这场前所未有的股灾暴露了当时市场机制的脆弱,尤其是程序化交易和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在市场下跌时引发了恶性循环。
然而,正是这场危机,促使美国引入了一系列关键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如今仍然是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熔断机制的推出,使得市场在剧烈波动时能够短暂停止交易,避免恐慌性抛售的蔓延;股票和期货市场之间的协调机制改善,帮助跨市场风险的更好管理;全球交易所间的信息传递更加迅速透明;结算与交收程序的完善,也降低了系统性风险。这一切为美国股市提供了强大的“护盾”,让它能更好地抵御未来的危机。
到了90年代末,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再次掀起投资狂潮,特别是科技股的火爆推高了纳指一度上涨了近400%。互联网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获得了过高的市场估值。
然而,这种非理性的繁荣最终在2000年3月破灭,投资者开始抛售被高估的公司,一些互联网公司未能达到盈利预期或现金耗尽,因此恐慌性抛售蔓延到整个市场。纳指从 2000 年 3 月的 5,000 多点峰值跌至 2002 年 10 月的 1100 点左右,暴跌近 80%。美股市场损失约 5 万亿美元的市值,
这场泡沫虽带来毁灭性冲击,却也清除了大量缺乏基本面的投机公司,为真正具备盈利能力与技术护城河的企业创造了发展土壤。亚马逊、谷歌、苹果等公司在泡沫洗牌后崭露头角,逐步成长为引领全球资本流向的科技巨头,也标志着美股正式迈入“科技蓝筹”主导的新时代。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的又一次巨大的考验。9月29日,由于国会拒绝通过银行救助法案,创下当时历史最大单日跌幅。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幸好,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措施,并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金融监管。这些举措加强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为市场带来了重新崛起的机会。
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发,美国股市在短短33天内暴跌了34%,创下了历史上最快的熊市。然而,尽管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政府和美联储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和量化宽松措施来稳定市场信心,支撑经济复苏。尽管疫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但美国股市在经历短暂的下跌后迅速反弹,并创下新高,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韧性。
细数美股的历次危机,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再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与2020年的疫情冲击,每一次都曾引发剧烈震荡,甚至动摇市场信心。但每一次,美股也都依靠制度修复、政策响应和市场自我调节能力,重建秩序、走出低谷,并最终再创新高。
今天,虽然关税壁垒与全球贸易摩擦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波动不断,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健:就业市场保持强劲、企业利润仍具支撑力、消费韧性未减。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央行对市场的关注与干预意图明确。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在关键时刻缓和贸易态度,还是对白宫与美联储关系的调整,其核心都是维持市场信心、稳定资本预期。
因此,当前美股的回调,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一场系统性的再平衡。正如历史无数次所验证的那样,当市场因为恐慌而短期下跌,反而往往孕育着长期布局的机会。只要美国的制度根基、创新能力与应变机制依然存在,美股就有理由继续作为全球资本最具信任的避风港。
无需担心美国制造业高成本
这轮美股大跌,其中一个诱因,是川普再度提出大幅提高关税,强化“美国制造”回流战略。市场的担忧随之而起:如果美国执意推进再工业化,高企的人工成本是否会拖垮经济本身?物价是否会因此失控,最终反噬企业利润、压垮消费端?
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但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直觉陷阱。制造业成本上升确实存在,但将其等同于经济系统崩盘,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伪命题。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是什么支撑着一国经济正常运转?
这轮美股大跌,一个核心担忧是:在“美国制造”回流的背景下,高昂的人力成本会拖累经济,物价可能失控,进而冲击企业利润和消费能力。
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但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直觉陷阱。制造业成本上升确实存在,但将其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减速的主因,忽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力量,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判断。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是什么支撑着一国经济正常运转?
是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布局构建的低成本供应链?是贸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与资源配置效率?是资本对边际成本的压榨和对全球要素价格的套利?还是几十年来,美国企业所推崇的“轻资产运营 + 海外外包”的高回报商业模型?
这些因素都重要,它们是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石。但所有这些优势,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生产和消费能在体系内部闭环。一旦这一循环断裂,再便宜的供应链也无法持续创造真实的增长。
当前很多人担心:制造业一旦搬回美国,商品成本上升,价格变贵,普通人消费不起,经济运行将陷入瓶颈。这种看法听起来有逻辑,但经不起深入推敲。我们不妨做个极端设想:假如全世界只剩美国一个国家,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会不会因为工资高、成本贵,就导致系统崩盘?
答案是否定的。只要人们仍愿意生产、仍有消费能力,只要收入与成本之间维持动态均衡,经济循环就不会停止。价格上涨的同时,收入也会上升。生活成本提高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价格结构、工资结构同步抬升。这不是系统瘫痪,而是结构重塑。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贵不贵”,而是“能不能自洽”。只要这个系统能让生产端赚到钱、消费端花得起钱,中间的流转机制稳定,那高成本就是一个可以消化的变量。美国经济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而不是一味追求便宜却不断外泄的增长模型。
制造业回流所带来的,不只是高成本,而是高工资、高就业和高质量的内需市场。短期看,确实会有通胀压力。但中长期来看,这代表着美国重新激活了被边缘化的蓝领阶层。过去几十年,美国底层工人被全球化所替代,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但就业结构断裂。大量依赖政府福利维持生活的工人群体,并未成为经济的正向推动力,反而拖累了财政,削弱了本土消费基础。
这也是“美国制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成本,而是分配。
特朗普所推动的不是简单的关税壁垒,而是一种战略性的结构转向:把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模式,转变为市场化的工资收入机制。与其由政府给底层发钱,不如让资本通过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间接把收入转回生产者手中。这是一种更可持续的结构交换。
在这样的新体系下,富人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但他们也因此收获一个更加活跃的国内消费市场。而底层工人则从边缘人变为市场的主力,他们不再是财政的负担,而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这一逻辑的本质在于:经济不靠压低成本,而是靠扩大参与。
当制造业回流,美国经济将重建一个“工作—收入—消费—利润—投资”的完整链条。这比靠政府举债发钱、靠进口商品低价刺激消费,要健康得多,也稳定得多。
有人说,美国制造养不起美国人。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没有让他们参与制造。他们被外包和自动化挤出产业链,被福利系统安置在边缘,但从未真正融入增长逻辑。而如今这场制造业重建,本质上是一次对社会结构的再平衡。
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造就了美国资本的空前繁荣,那么接下来的“美国制造”,可能带来的,是消费结构的重构、就业体系的重塑和社会阶层的重新稳定。美国的强大,从来不在于它没有问题,而在于它有能力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混乱中重建秩序。
这轮市场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对旧逻辑的情绪释放,而非对现实经济的理性定价。真正理解“高成本背后的结构机会”的人,反而会在波动中看清方向:制造回流并不会拖垮美国经济,反而可能成为下一轮长期红利的起点。
所以,与其问“美国制造能不能负担”,不如问一句更本质的:美国有没有能力,把高成本变成高质量的增长?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对美国有信心吗?你怎么看这次回调?你是否会抄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